懷孕了,但是問題很大。

小宮女一朝穿越,回到了皇后小時候。她能否扭轉皇后和皇上離心的局面?點擊藍色字:《商女皇后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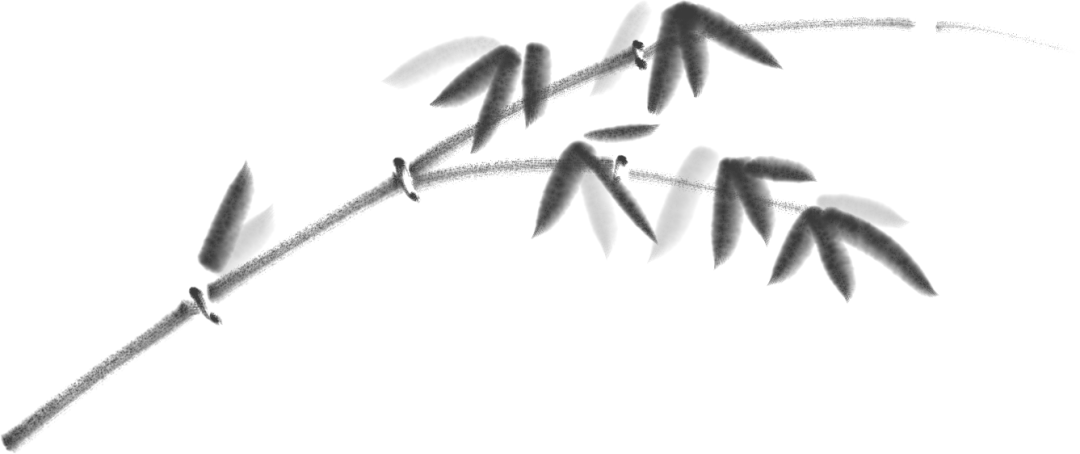
接上集
“所以你說,我是不是很該死,仗着他是我哥、仗着從小長大的情分、仗着他對我下不去手,我才那樣肆無忌憚奪了他的妻!”
“你問我怎麼想?他是我的親哥哥,是我在這世上僅有的血親,是除了你之外我最親近的人,他要造反,我就做他的第一個兵,他要這江山,我就算死也一定會幫他打下來...”
“這是我心甘情願償還的代價…我的命給他了…”
第 54 集
說到後面,越來越沒聲了。
竟是睡過去了…
這些話,想必在他心中憋了許久,不得見天日,隨便單拎一條都足夠讓他萬劫不復了。
我將他放平躺在牀上,手指輕輕撫上他的眉眼,心疼極了:“傻子。”
第二日,他醒來揉着昏聵的腦袋,問我:“我昨晚沒說什麼胡話吧?”
我盈盈一笑,端了茶水遞給他:“睡得比豬還死。”
見他皺着眉頭思考着什麼,我笑他:“怎麼,你昨晚說了什麼我不能聽的嗎?”
他將碗中茶水一飲而盡,揉了揉我的臉,寵溺一笑:“哪有?只是我昨晚做了許多亂七八糟的夢,到現在還暈着。”
我把他按倒在牀上:“既然還暈着,那就繼續躺着,也別去上朝了,讓多榮去給你告個假。”
他一聽順勢摟過我,一陣親暱,片刻過後:“不行不行,我今天有事,還得進宮一趟!”
說罷從我身上爬起來洗漱,等一切收拾妥帖,捧着我的臉使勁吸了一口:“等晚上,晚上我回來,咱們繼續!”
我啐他一口:“繼續什麼?”
他促狹一笑,瞥了一眼我的腹部:“你說繼續什麼?當然是造小人啊!兄長和皇上都當爹了,就我一個光桿司令,他們聊子女,我幹什麼?傻站在一邊看啊?”
“走啦!”
我摸了摸自己平坦的小腹,心生鬱悶,我倆這麼勤,怎麼連一點動靜都沒有呢?
夜裏謝時郢沒有回來,遣多榮回來報了個信。
“新野戰事喫緊,候爺從宮裏出來,又馬不停蹄的趕去了將軍府,和將軍商量新野戰事去了,說是今晚不回來了,讓夫人自個兒先休息。”
我心中煩悶,這新野的局勢,都兩三年了,還是一灘爛泥,朝廷投入了許多兵進去,始終未能剿平這波反叛勢力,而且還有了愈演愈烈的局勢。
朝廷一直沒有派重兵去攻打,領兵人選也一直懸而未決,瞧着謝時郢又是進宮面聖又是去將軍府徹夜未歸,我心裏有一些隱隱擔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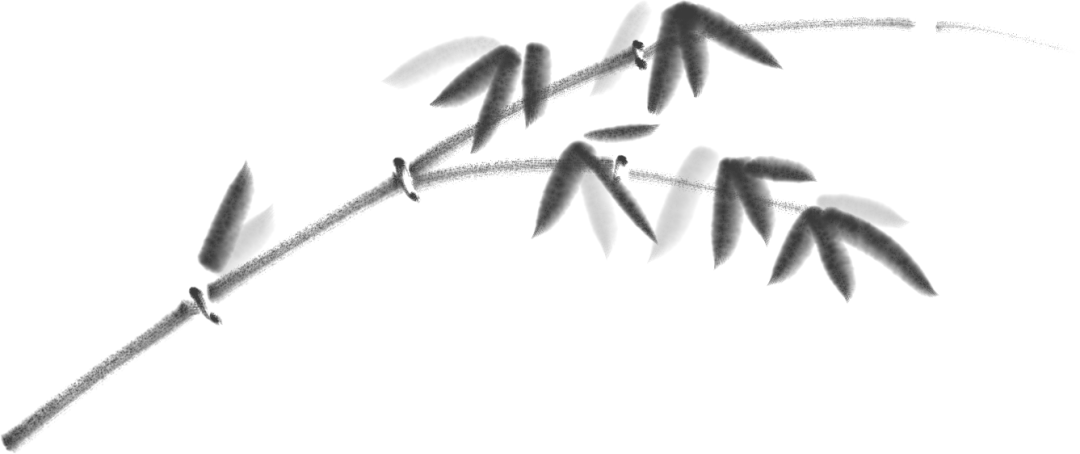
第二天下午,謝時郢纔回府。
眼睛下面一圈青色,估計是一夜未睡。
他拉我坐下,神色有些凝重。
“給你說件事,我可能要出趟遠門一段時日.....”
我心裏咯噔一下,果然被我猜中了。
我聽見自己的聲音悶悶:“什麼時候走?”
“後日。”
我扭過頭去不想看他。
他將我身子扳正,面向着他直視着:“別這樣,你這樣我捨不得去了...”
我總算明白了當年琴卿嫂嫂面對着哥哥去新野時的心情,只有身臨其境纔會感同身受。
“朝中有那麼多會打仗的老將,爲什麼偏偏要你一個半路子出家的文臣當統帥去平叛?”我小聲嘀咕着,心裏又難受又擔憂。
“原因有兩個,一是我年初的時候剿滅了滄河水匪,在朝中還算有些聲望,北邊要留盧令飛和曲不然守着,以防烏丸南下突襲,剩下的擅長打仗的幾個老將都七老八十,連陛下都喊不動他們,這事終歸要落到兄長頭上,再然後就是我要和你說的第二個原因了,兄長剛做了父親,母女兩個正是需要有人照顧的時候,我想替他分擔一些…”
我想起昨晚他說的那些醉酒話,眼淚不爭氣的掉下來:“你記掛着他人母女有沒有人照顧陪伴,你自己的妻室和桉桉呢?”
他用指腹幫我拭去眼角淚意:“我答應過你的,我一定珍惜小命,平平安安。”
“好啦,快別哭了,來親一口,我這一去不知道會有多久親不到你的粉嫩小口...”
說罷作勢捧過我的臉,我沒忍住,噗嗤一聲笑出了聲,又哭又笑捶了他胸膛幾下:“你老這樣不正經...”
謝時郢緊緊抱住我,我貪戀他的懷抱和胸口的溫熱,一時之間,兩人就這樣抱着,相顧無言。
當天夜裏,他格外溫柔,只來過一次我就不讓他再來了,外出打仗,最是需要養精蓄銳,我可不想他因爲這種事過度,對他的身體健康有所影響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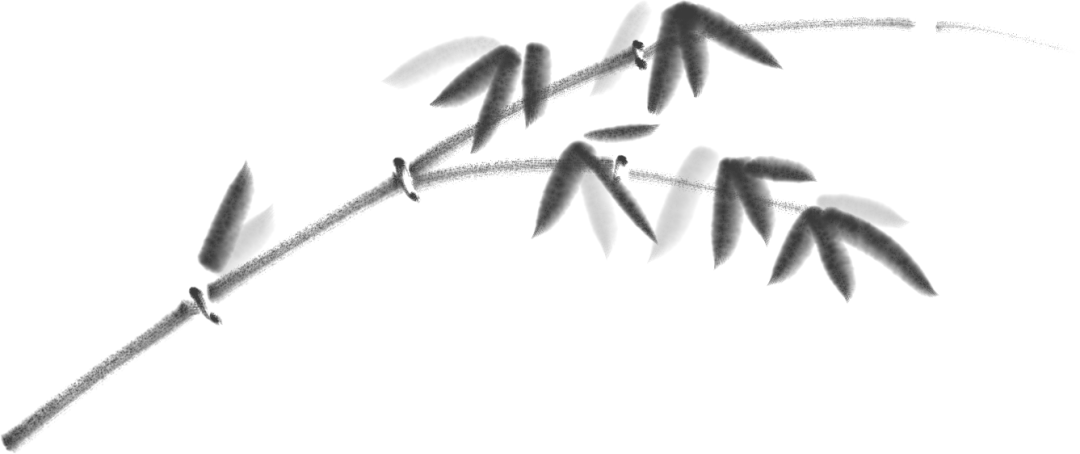
此後兩日,他都去了將軍府,商量戰事部署,每每都是半夜回來,我摸到身邊有人,睡得也格外安心,早上天不亮,再一摸,身邊空空蕩蕩。
出征的前一晚上,他破天荒的回來很早,洗乾淨後,摟着我躺在牀上,什麼都沒做,此前我告訴過他,這幾日可能是小信之期快來了,肚子難受的厲害,有些隱隱痛意。
他憐惜我,就真的只抱着我睡了一晚上。
屋子外面打更的剛敲了二更,他將我摟緊了些:“我還能再抱你兩個時辰左右,寅時我就得出門去校場點兵了。”
“我能去送你嗎?我還沒見過你出征。”
他想了一會搖頭:“你還是別去,天都沒亮,外面涼,小心受了風。”
好吧,不去就不去,去了目送着離開,我又得難過。
寅正時分,他起身,我因爲肚子不舒服,左右也無睡意,起身幫他更衣。
送他出府之後,我扶着門再也支撐不下去,趕緊喚來新月:“我肚子疼得厲害,去找郎中來!”
新月不敢耽擱,趕忙領了兩個僕從出門去找郎中。
等人過來的時候,我痛得冷汗淋漓,暈了過去,暈之前還納悶,這次月信怎麼會這麼痛?
悠悠轉醒,一個我從未見過的郎中正在把脈,看我的神情一言難盡。
我不疑有他,問郎中:“我每回來月信都要疼上一疼,怎麼這次這麼嚴重?”
郎中五十開外,其貌不揚,稀稀疏疏幾根鬍子有花白之色,只一雙眼睛還算有些神采,此刻正搖着頭,覷我一眼,有些傲然之色:“夫人你來沒來月信,自己不清楚的嗎?”
我愣了愣,看向新月,我剛換下的衣褲上面沒有血嗎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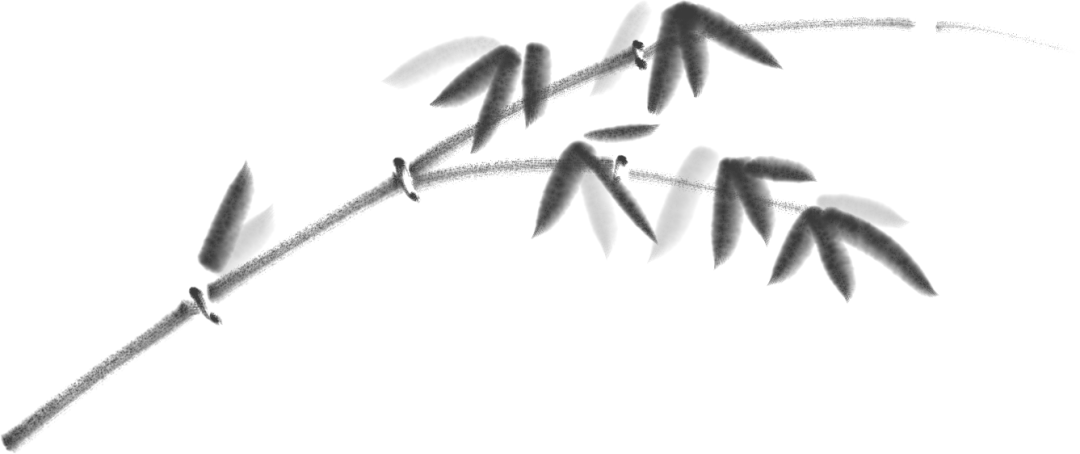
新月也是一臉懵:“夫人您說什麼呢?您沒來月信啊!”
我倆齊齊看向郎中,見他捋着下巴上的白鬚,朝我翻了個白眼,頗有些無奈道。
“這位夫人,房事需節制,你都是懷有身孕的人了,切不可再由着夫君性子胡來,這次幸虧是你們請老夫來得早,又是給你施針又是一貼猛藥下去,才穩了你的身子,要不然啊...”
這郎中搖着頭,一臉諱莫如深。
我全然沒在乎他的態度,關注都在他的話語上,只聽到了他前半句,一開始還不確信,問向新月:“他說什麼?”
新月聽的真切,喜上眉梢,差點沒蹦起來:“夫人!夫人!他說您有喜啦!”
我怔了半晌,半天沒反應過來,失神的看向郎中,他淡淡向我頷首,又語重心長的囑咐了我兩句:“記住我剛剛說的,你這胎還不穩,切不可再行房事了!”
我訥訥的點頭,心裏只有一個聲音:我要告訴謝時郢,他要做父親了!
“現在什麼時辰了?”
新月看了一眼外面的天色:“估摸着快辰時了吧!”
“侯爺他們拔營了沒?”
我起身穿鞋,朝屋外走去,身後的郎中長嘆一口氣,無奈的搖搖頭。
我坐在侯府的馬車上,座位上放着軟墊,一路載着我到城門口處。
一路上我回味着這郎中的話,還是覺得十分不可思議,我居然懷孕了?
我問新月:“這郎中哪裏找的?靠譜麼?”
新月道:“夫人您事出突然,那個點藥堂鋪子都沒開門,只在臨街有個擺攤的野郎中在,我就…”
我半截話憋在嗓子口,遊醫郎中啊…
也行吧…
話趕話就到了城門口處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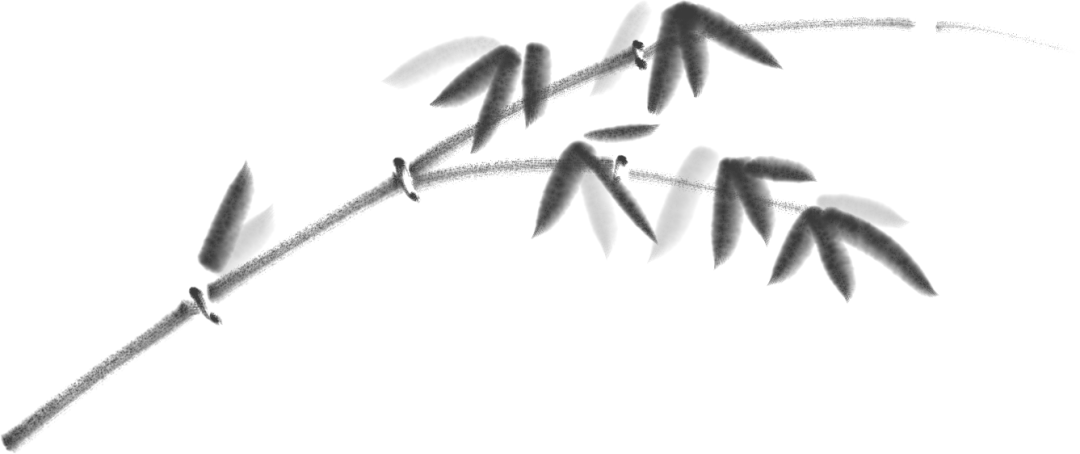
新月小心翼翼的扶着我,我推開她的手,訕笑一聲:“搞太過了哈,我這才哪到哪。”
待登上城樓,我極目遠眺,大軍已然開拔。
最前方的統帥在我眼裏只剩下一小點,我心中悵然若失,終究還是沒能趕上。
手輕輕放在小腹之上,在那裏,正孕育着一個我和謝時郢的情感結晶,我癡癡望着前方,心中默唸一定要平安歸來,我和孩子等着你。
下城樓的時候,遇到了謝時垣。
他騎在馬上,一身輕盔,在距我不遠的城門口處,與我目光相觸。
我本能的想回避,但心中突然有個聲音在說,該面對的總要面對,我不可能避而不見一輩子。
我垂首,深呼吸一口氣,再抬起頭時,他已下馬,牽着馬走至我跟前。
新月警惕的看着謝時垣,小心膽怯的將我護至身後,我輕輕拂開她:“你先上馬車上等我。”
清晨的城門口已有了沿街叫賣的攤販吆喝聲,謝時垣站在我面前,高大的身影將我籠罩住。
這是我和他自和離之事刺傷他之後的首次單獨會面。
他還是一如既往的冷漠和疏離,我只得先開了口:“聽說將軍前些時日做了父親,還沒有恭喜你。”
謝時垣聽到時,面上的神情有所緩和,不再像冰雕泥塑,看來他是真的很喜歡他的女兒。
他動了動脣,還是沒開口。
我笑一笑,有些心結終究是要自己解開的。
就像我此刻,嘗試着坦然面對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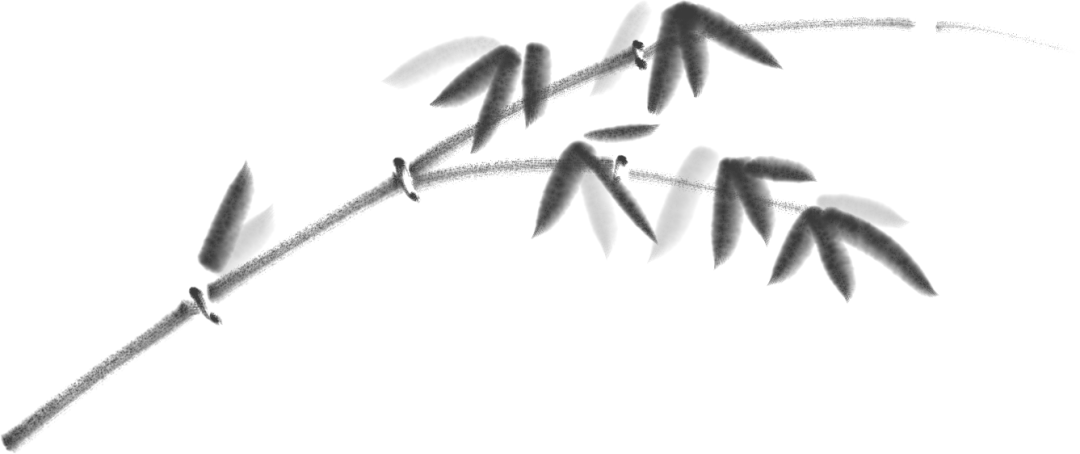
“謝將軍,我爲我當年之事一直欠你一句道歉,如今我們都有了新的開始,我今天面對着你,鼓起勇氣放下前塵,我希望你也一樣,下次我們再見面,可以一笑泯恩仇。”
言罷我直視着他,神態自若。
他玩味的勾起一絲嘴角,重複了一遍:“一笑泯恩仇?”
“我與夫人之間何來的恩?又是什麼仇?”
我樂了,大約知道他是個什麼態度了。
“如此,便好。”
在他眼裏,我與他之間徹底兩清,再無過往,相逢即偶遇,沒有旖旎,也無仇怨,這是最理想的狀態。
該說的已說,再無多話。
我朝他福了福身子,準備上車。
謝時垣在身後喊住了我,清冷又剋制:“夫人留步。”
我回頭,微微詫異,他向我伸手,掌心躺着一枚腰牌,赫然刻着一個燙金大字:“敕”。
這是給我的?
他的面目表情依舊冷的沒有溫度,說出的話硬邦邦:“憑此令牌可自由出入將軍府邸和宮城。”
見我猶豫,遲遲未接,半晌他補充了句:“阿郢離京,你一個人若是遇事不決可憑此腰牌出入自由。”
我有些怔仲,愣了好一會。
以前我總是希望他能對我多一些包容與保護,但大多數希望都落了空,如今我倆徹底沒了關係,他卻拿着出入自由,不受挾制的令牌爲我開路。
這算什麼呢?
罷了,想太多,又要生好些迷惘。
我微微一笑,接過令牌,朝他點頭示意,疏離客氣的模樣好似得他真傳。
“如此,謝過將軍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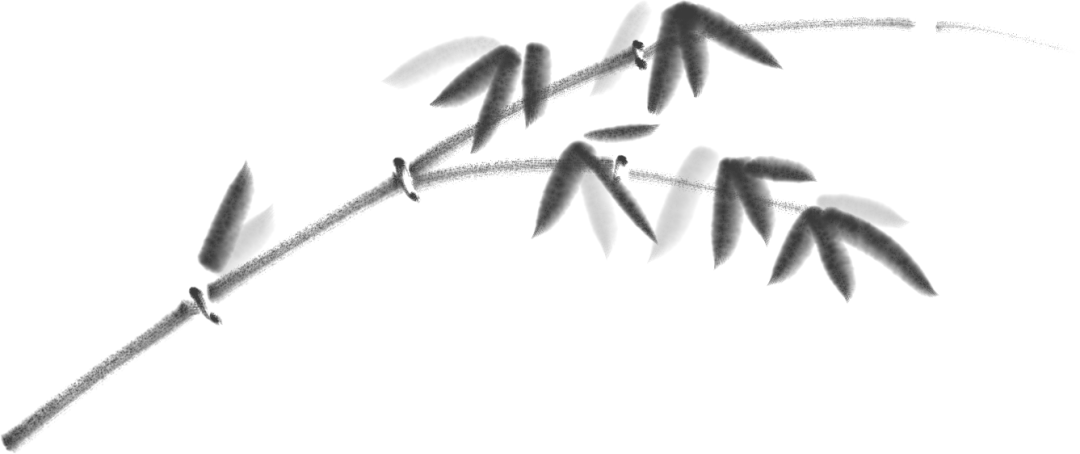
馬車悠悠駛離,朝着憫北侯府的方向歸家,我蔫蔫的靠在馬車後背軟軟的靠墊之上,心下愁緒纏綿肺腑,暗暗盼起了日子,十月懷胎,也不知道謝時郢這仗要打多久,能不能趕得回來迎接我們第一個孩子降世。
新月撂下簾子,同我小聲說道:“夫人,大將軍還立在街口看着咱們馬車呢......”
嗯?
我心裏嘁笑一聲,將那若有若無的猜想按了下去,眼前人是心上人,眼前事...就是養好自己的身子,等着和這個小傢伙見面。
至於其他的,不過是前塵往事一場空,風一吹就散了。
“回家吧...”
侯府門口,新月小心翼翼扶我下車,還沒等我腳站在地面上,一抹藍色衣裙的人影倏得停在我面前。
撲通一聲,那人跪了下來。
“大奶奶!奴婢見過大奶奶!”
滿月跪在我面前,結結實實地朝我磕了三個響頭。
抬起小臉,一雙霧氣盎然的眼睛,哭得梨花帶雨。
我心中詫異:“你怎麼跪在這?快起來。”
“新月,帶她進府。”
侯府正廳裏,我坐在首座,新月立在身後,滿月我讓她坐在下首位置。
她的身契謝時郢已經還給她了,現在她不必以府中奴僕自居。
她坐在椅子上有些侷促不安:“奴婢早先聽聞大奶奶回京了,只是一直沒有過來得見,今天貿貿然過來,衝撞了大奶奶,是奴婢罪過。”
起先坐了許久的馬車,如今又是坐在椅子上,總覺得有些坐不住,不知道是不是懷了孕的緣故,睏乏的很。
我揉了揉眉心,有些苦惱:“別再叫我大奶奶了,你也不是侯府奴僕了,不用自稱奴婢...”
滿月惶恐,小心回答:“是...”
“夫人...”
“是奴...是我一時沒有改習慣,夫人,您這一年多都去哪了啊?滿月以爲您....”
我擺擺手,不想再提過往,指了指新月:“回頭你們姐妹倆敘舊聊一聊,我就不和你細說了。”
新月笑意盈盈,過來拉滿月的手:“滿月姐姐,你自出了府去,許久都不曾回來看我和杏姑一眼,我還當你忘了侯府呢。”
滿月笑得訕訕:“怎會?”
她看向我,滿眼關切“夫人可還好?杏姑呢,她還好嗎?”
我點點頭;“還是老樣子,湯藥吊着。”
我從滿月進府,就看她欲言又止了好幾次,猜她定是有事纔來侯府,不然就憑剛剛新月說的,離府大半年,一次都沒回來看過她和杏姑。
我在等她自己開口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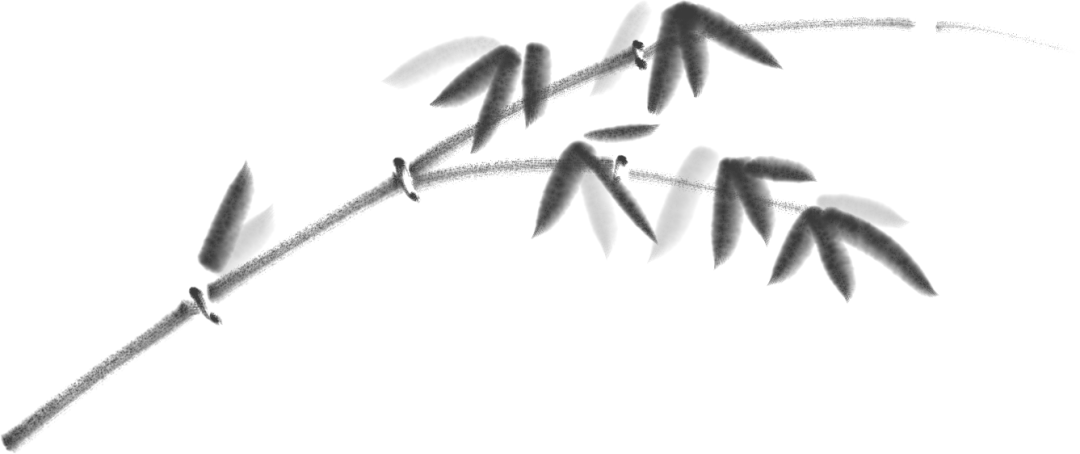
好半晌,她才期期艾艾的開了口“夫人,你空了去瞧瞧邵大哥吧!我也是實在沒法子,纔來求到您跟前...”
我眉心一皺,焦急問道:“哥哥出什麼事了?”
滿月身子一歪,再一次跪在我跟前,淚眼婆娑:“方夫人離去後,邵大哥像是失了魂,整日渾渾噩噩,生了好大一場病,這些滿月都不帶怕的,總會好起來的,可現在邵大哥病好了之後,整個人像是變了一個人似的,日日酗酒,夜宿花船,有好幾次都是我連拖帶拽將人拖回來的...”
“滿月知道,我無名無分,不敢奢求什麼,只求留在邵大哥身側做個灑掃做飯的粗使丫鬟就行,但看到現在的邵大哥好端端的一個人變成這樣,我是一點辦法都沒有啊!昨天夜裏,他甚至爲了花船上的伎人,與人打鬧起來,險些花船,如今被人困在花船上,老鴇不肯放人,說是要賠償花船的損失,和打人的藥錢,我實在是沒有辦法了,才求到侯府來!”
我猛然站起來,又驚又駭:“你爲什麼不早點告訴我!”
“他是我哥哥,邵家還差那幾個花船銀子錢嗎?”
“爲何昨晚事發之時,不來侯府找我!”
突然動了怒,此刻只覺得小腹有些隱隱不適,我倒吸一口涼氣緩了緩,抓穩了新月胳膊才站穩了些。
新月小心翼翼扶着我坐下,在我身後又塞了軟枕讓我靠着。
滿月張惶失措:“我...我...我聽到外界傳言夫人的事,我不敢來找您,怕給您添了麻煩,沾惹上是非...”
唉,又是一個傻子。
“罷,不說那麼多了,哥哥現在人在哪,帶我過去。”
盡都是些不省心的,我起身準備動作。
新月攔住我:“夫人,忘了那郎中怎麼說的嗎?您這身子哪裏禁得起奔波?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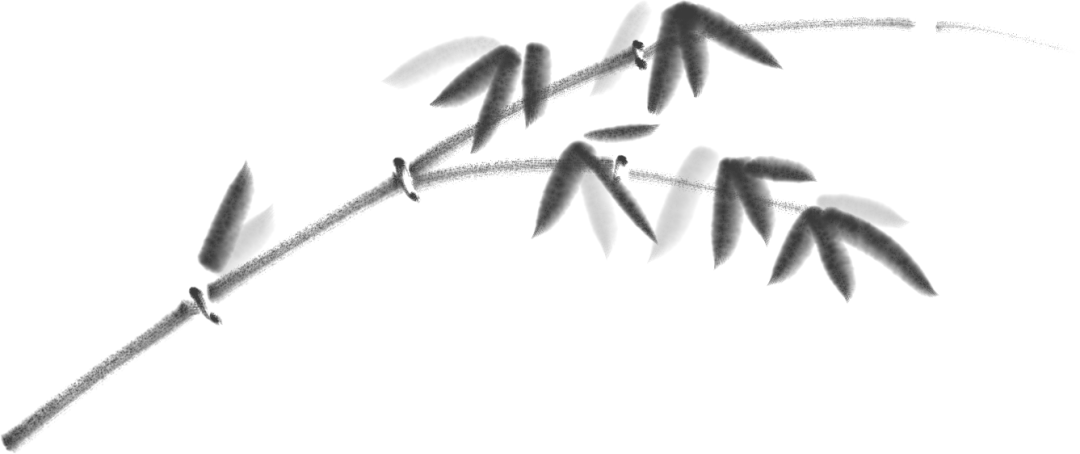
我扶着椅子扶手,剛準備起的身又慢慢往後靠了靠。
郎中說我這胎不穩,需靜養,可這眼前一堆事,我如何能定的住心神?
滿月瞧見了我的異樣,目光漸漸移向我的腹部,眼底閃過一絲驚喜光芒:“夫人您...有啦?”
我微微點了一下頭。
滿月臉色馬上變了,自扇了個嘴巴:“那我真是該死,這般莽撞,害夫人擔驚受怕!”
我抬手製止她:“快打住吧,別磨蹭了,哥哥還等着人去救,新月,去取府中對牌過來,讓賬房支些銀票,你和滿月一同過去,若是那邊人還不依不饒的,你就拿令牌給他們看。”
我把謝時垣給我的令牌放在新月手裏,權傾朝野的鎮北大將軍令牌,對付個花船那種勾欄地方應該是夠用的。
完事,我囑咐滿月:“將哥哥救出來,直接帶他來侯府,我要見他!”
兩人得令,揣着銀票,由滿月帶路,去了花船。
那花船我聽過一耳,有別於其他地方開在煙花柳巷的妓館,這花船自然是開在河面上的。
沿着鄴京城外圍的煙波河,大大小小的畫舫船隻在這裏連成一片,裏面的人能歌善舞,小有才情。
聽說比之尋常妓館更添別樣風情,文人騷客都喜歡去這裏尋樂了。
我一個人呆呆地坐在椅子上,心裏不是滋味,邵簡好好的一個青年才俊,朝廷肱骨怎麼變成了如今夜夜宿柳眠花的浪子。
琴卿嫂嫂的驟然離世,真的帶走了哥哥最後一絲理智麼?
阿萍趴在門口,露出半張小臉,瑟瑟看着我:“姐姐,你還好嗎?”
我朝她微微一笑,伸出手:“過來。”
阿萍走過來,在我身側蹲了下來。
“說實話,我感覺並不太好。”
藉着她手上的力,緩緩站起身:“扶我回房休息。”
思來想去,我還是再次請了那郎中上門。
這郎中姓章名乙,不比以前京中的黃大夫好相處,性子頗有些傲氣,但我想,恃才傲物嘛,也許他的醫術擔得起這份傲氣。
給我把完脈,章乙冷笑一聲:“夫人還是顧惜自己的,曉得把老夫再次請回來。”
我自己的身體當然知道什麼狀況,眼下偌大的侯府就我一個主事的,我若是自己不顧惜自己,如何保住我腹中孩兒。
章乙起身在案桌上洋洋灑灑寫了一篇藥方,吹乾後遞給我:“夫人能把我二請回府,想必也是信我的,那老夫也不藏着掖着了。”
我點點頭,示意他接着說後面的話。
“夫人這胎會很艱難。”他直言不諱,我只覺得如當頭潑了一盆涼水,寒氣從腳底升騰起。
我將藥方遞給小萍,讓她去找府中管事多榮,帶着她去抓藥熬製。
等人走後,此間就剩我兩人。
我嚥下一口唾沫,忐忑問到:“如何個艱難法?可有得醫?”
未完·待續
懷孕了,但是,依舊很難。怎麼辦?
點贊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推送喲


